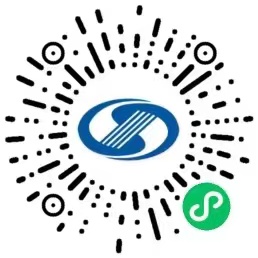藍海沙龍|互聯互通背景下平臺封禁行為線上研討會成功舉辦
2021年08月30日 18:23
8月27日,中國互聯網協會召開了第238期藍海沙龍——互聯互通背景下平臺封禁行為線上研討會。會議由中國互聯網協會副秘書長宋茂恩主持,中國科學院大學經管學院教授、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呂本富,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競爭法與競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孫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許可,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競爭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翟巍,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經所監管研究部主任李強治,中國社會科學院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國家計算機網絡應急技術處理協調中心副研究員張震,中國消費者協會投訴部謝龍,《比較》雜志研究部研究員陳永偉等專家參加會議并發言。
宋茂恩介紹了會議背景。他表示,互聯網平臺在我國經濟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與此同時,在平臺經濟領域中也出現了較為嚴峻的壟斷問題。最近媒體關于平臺封禁行為及平臺間關于封禁行為訴訟的報道,引發社會反響。有觀點認為,平臺爭奪用戶和流量的趨勢不斷加強,大型平臺之間的封禁行為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后果,消費者的現實利益受到侵害,平臺封禁是互聯網平臺權力日益膨脹的直接體現。也有觀點認為,平臺為了成為行業贏家,花費了巨大的成本和代價,如果后來者可以無償獲得平臺資源,對先行者也是一種不公,反而傷害到對創新的激勵。因此,如何把握平臺封禁與平臺互聯互通的邊界至關重要。
李強治表示,與國外相對開放互通的網絡空間不同,我國頭部平臺之間長期的封禁策略,使得形成特有的“網絡孤島”現象,即平臺“生態內開放互通、生態外隔離封鎖”的情況,其根本原因是平臺間對網絡流量控制權和變現權的爭奪,這也是我國平臺領域無序擴張局面形成的重要誘因之一。目前,這一現象在我國已經陷入了一種負反饋狀態,很難通過行業自律和自由競合來形成開放互通的網絡格局,需要從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加以有效治理和分類引導。
陳永偉表示,封禁行為從經濟本質上看是平臺開放與封閉的選擇問題,分析平臺的開放與封閉,要比較個人最優和社會最優,如果差別較大,封閉造成社會福利損失,就需要政府干預。針對封禁的規制,要分類看,《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電子商務法》三者應用的條件是不同的。針對“守門人管制”,要謹慎處理。對于“囚徒困境”類的相互封禁,在法律規制的同時,政府出面進行協調也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謝龍表示,在討論平臺封禁時,也要重視中小企業平臺的封禁行為以及被封禁的經營者。封禁行為影響消費者的知情權,限制消費者獲取信息的渠道,使其不能更全面地了解信息。在平臺因封禁行為獲取收益時,用戶作為數據產生者是否有收益權值得思考。此外,具有完善生態系統的大型平臺在平臺治理中行使了公共管理的權力,可以借鑒濫用“行政權力”的方式對其進行規制。
劉曉春表示,如果需要為平臺設立類似于守門人的義務,可以通過立法、平臺承諾或者自律公約,賦予平臺中立和開放的義務。此外,可以根據平臺行業的類型化考察平臺自治的邊界,通過對格式合同干預或運用其他法律和技術處理平臺封禁這一問題。運用不同的法律工具和政策在事先對平臺邊界和法律干預的框架性做法,有些可以先從司法個案中進行突破。
呂本富表示,從宏觀上探討平臺封禁包括兩方面,一是平臺有哪些種類。平臺的三大種類分別為:人與信息的鏈接、人與商品的鏈接、人與設備的鏈接。二是哪種封禁行為需要國家干預。要分清哪些是市場行為,哪些是損害社會福利的行為。對于前者,靜等其變;對于后者,選擇合適法條進行規制。具體而言,干預有三個標準,封禁是否降低就業、創新和市場活躍度,封禁是否損害消費者利益,封禁是否損害中小企業的利益。
張震表示,互聯網的極速發展對法律法規體系的前瞻性設計提出了極大挑戰,需要結合互聯網演進規律,創新法律體系規劃設計,完善技術保障體系,建立互聯網平臺標準互通接口,實現平臺在互聯互通收益及風險方面的權責明晰,推動互聯網行業健康和諧發展。
翟巍表示,在司法訴訟中超大型平臺以其被訴封禁行為具有正當性為由進行抗辯,立法及司法機關應當強化其舉證責任,具體有四個標準:其一,顯著性標準:被訴行為能夠顯著提升社會公共利益;其二,不可替代性標準:被訴行為具有不可替代屬性;其三,最低限度標準:被訴行為產生的負面影響被限定在實現正當性目標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之內;其四,透明性標準:平臺應確保其實施的被訴行為動機、手段與后果的透明性與可查驗性。
許可表示,平臺封禁行為規制應當采取結構主義的觀點,既要區分平臺的不同層次,也要區分封禁的類型。就平臺層次而言,可分為物理層、邏輯層、應用層、數據層和信息層;就封禁類型而言,可分為限制同一層次的互聯互通,以及下一級層次歧視性、不中立地對待上一級。總體而言,從物理層到信息層,不得封禁的共識度逐漸降低,其合理性判斷應逐漸審慎。
孫晉表示,對于排除封禁、實現互聯互通的基本立場持肯定態度,但要注意防止過度監管可能導致的平臺“絕對平均主義”傾向。激勵性監管、監管前置和全程監管引導平臺合規經營在效果上事半功倍。此外,我國平臺經營模式和發展生態與歐美相比區別明顯,在立法、法律分析和監管實踐方面也一定具有特殊性,這是不容忽視的。
通過聽取各界專家的充分研討可以發現,互聯網平臺經濟新特點使該領域的競爭區別于傳統市場競爭,以平臺封禁行為為代表的新興問題使現有法規的適用與執行遇到新挑戰。對待平臺封禁行為,要分析其對行業發展、消費者權益產生的影響,在現有法律規定的基本框架內厘清其所適用的法規內容,以確保制度效用最大限度的發揮,并通過完善立法與持續監管引導形成互聯互通的行業規范,推動互聯網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為推動創新增添助力。